子午岭,让他无法走出的胎衣之乡——访作家高凯
2022-11-04 15:44:32
来源:西部大开发杂志
今年9月,与作家高凯见面得知他的长篇报告文学《绿子午》由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这部作品是中国作协2021年定点深入生活项目,旨在倡导“大森林大子午岭”的生态观,是作者继《拔河兮》《战石油》两部国家重大题材创作项目之后由同一个出版社推出的“春风三部曲”的第三部纪实文学力作。
生于子午岭腹地合水县的甘肃庆阳籍作家高凯,历时三个多月深入陕甘子午岭60个林场和4个国家级生态保护区进行了深入扎实的采访。《绿子午》是一部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主题长篇报告文学作品,作品通过追溯陕甘两省子午岭发展历程,对新中国成立后陕甘革命老区人民在子午岭森林保护、建设方面的成就以及子午岭林区改革发展和一线职工生产生活进行全方位记录,具有史诗的宏阔和深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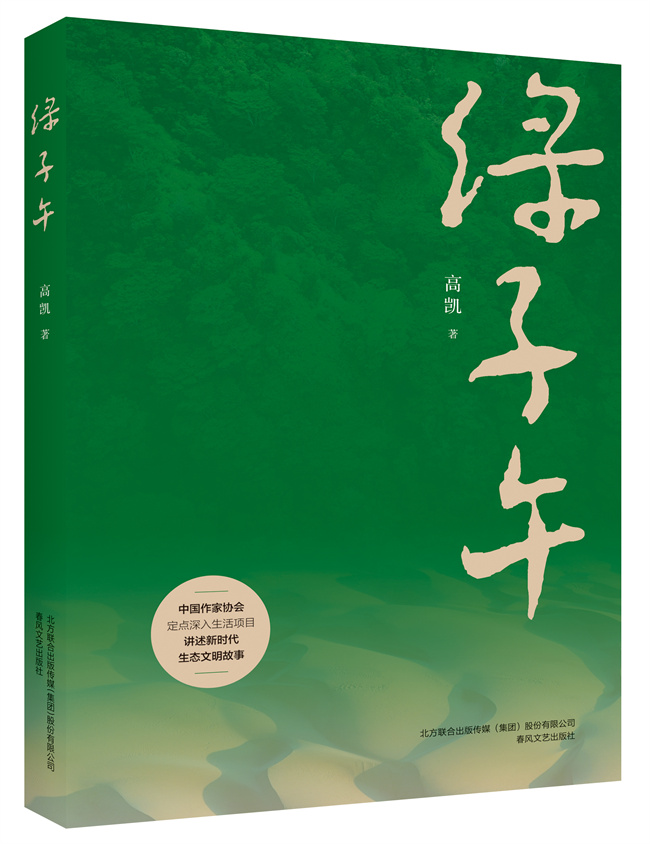
由作家高凯创作的陕甘子午岭第一部生态长篇报告文学《绿子午》
《绿子午》是一部非写不可的选题
沿着子午岭之路,作家高凯回到了童年的大森林里。他生在、长在子午岭。他的子午岭之行从童年就已出发。可以说他从子午岭开始,《绿子午》从他开始。在这中间一个世纪的时空里,绵延着一片森林缓慢而苍茫的年轮,横亘着包括他在内的几代人根深叶茂的林海守望。
在他童年的记忆里,最稀缺的生活物资,除了粮食,就是水和柴火。这三样东西,可谓人之命脉,互为勾连,缺一不可。好在,最大的粮食灾难被他躲过去了,可柴火之苦比缺水更甚。那时候,生产队方圆最少30公里以内的树木和野草被斫完了,人们只好去子午岭拉柴。在那个近乎荒蛮的年代,子午岭几乎被“掏空”。

作家高凯
作为当代知名乡土诗人,高凯从事文学创作40年来,先后出版《心灵的乡村》《纸茫茫》《乡愁时代》《高凯诗选》《童年书》《拔河兮》等诗集、散文、报告文学和绘本等著作18部。其中,这首老少咸宜的《村小:生字课》是高凯的代表作,2000年与高凯的其它12首诗刊于《诗刊》10月“每月诗星”专栏。2002年获第五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该诗发表20年来,一路走红,每年至少有5家权威文集选载,迄今被收《中国文库》《儿童文学选读》《共和国70年儿童文学短篇精选集》等百余种选集、典籍、小学阅读教材和大学儿童文学教材。央视CCTV7曾经推出同名诗剧。诗人家乡甘肃省庆阳市收入市志。重庆市永川区汇龙小学将其刻入石碑立于校园。2018年元宵节北京大学新诗春晚情景剧演出。浙江、湖南和山东等省的小学教师中进行推广阅读,影响广泛。充满自然、纯真与温情的童年随笔《高小宝的熊时代》,是高凯回顾自己童年时代的一部回忆性的作品,被译为英文由伦敦卡兹班出版社出版。
相比诗歌创作,高凯近年认为报告文学是时代的一面镜子,新闻性和文学性兼而有之,更适合纪实类文学创作。2019年,中国作协安排他前去采写甘肃省古浪县八步沙“六老汉”三代人治沙造林先进事迹,他很快圆满完成任务,并在《人民日报》“大地”副刊“时代楷模”栏目发表。这次成功尝试,对初涉报告文学创作的高凯是一次极大鼓励。接下来,他顺利完成中国作家协会定点深入生活项目《拔河兮》和《战石油》的两部长篇报告文学的创作。
正是有了之前数部报告文学的成功尝试和积淀,家乡子午岭开始进入他的创作视野。高凯说,子午岭是他永远无法走出的胎衣之乡,他一直没有忘记自己是一个子午岭人。他的精神之根留在子午岭森林深处,完成中国作家协会定点深入生活项目——长篇报告文学《绿子午》的创作,是一部他非写不可的选题。
子午岭永远是一个浑然一体的自然存在
选题立项之后,对于高凯,这无异于一次冒险。奔六十的人了,对其体力必然经受一次考验。在2021年6月14日至9月30日之间的时间里,高凯本着“大森林大子午岭”的精神,分三次跨越陕甘两省走完了子午岭的60个林场和4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最后写成了这个可能是迄今唯一一篇完整的关于子午岭生态文明建设成果的报告文学——《绿子午》。
高凯说,长篇报告文学《绿子午》的写作初衷或意图,旨在展示一个“大森林”和一个“大子午岭”。子午岭虽地跨陕甘两省,但在他的写作中不分陕甘。他的期许是,让大森林回归大森林,把子午岭还给子午岭。
子午岭总面积2.3万平方公里,其中,位于陕西1.21万平方公里,位于甘肃1.09万平方公里。子午岭在黄土高原的腹地,子午岭森林为黄土高原中部地带重要的生态公益林,也是黄土高原保存比较完好的天然植被区,像一道绿色屏障。
高凯分析认为,从自然界的法则看,子午岭不是属于陕西省或者甘肃省的,科学地表达应该是子午岭拥有陕西和甘肃,而不是甘肃和陕西占有子午岭。古老的子午岭不能被后世的行政区划分割,子午岭只能是一个浑然一体的自然存在。其间的隶属区划,只是人类社会在变,大自然并没有什么变化。高凯举例说,“树大分杈”是一个自然规律,但只是事物的一个现象,“分杈树大”才是事物的本质,其逻辑关系是,一棵树,不论大小,在其生长过程中只有不断分杈才能长成一棵树。但是,“分杈”却不能“分根”,必须同根而生方能长成一棵树。一棵独立的树必须如此,一片独立的森林也必须如此。
日月安详,静守自然。一代代子午岭人长年累月,“给山顶戴帽子,给山腰盖被子,给山脚穿鞋子。见缝插针,哪里没有树,就给哪里把树栽上”。如今的子午岭,林海起伏,古老的大森林丰富多彩。
有趣的是,《绿子午》的创作,高凯首先完成的是《送给七个小矮人的七首小诗》这一章节的写作。“孩子们都有一颗自带的大自然之心,我之所以把这些大森林的诗首先给孩子们,或者说给孩子们写了这些大森林的诗,就是希望告诉孩子们一个大森林的故事。”高凯说,以儿童视角写作,他是为了把更多小读者带进一个童话世界。书中所写的七个小矮人,像是是格林童话《白雪公主》中的小矮人,他们是大森林里最善良、最诚实、最勤劳和最勇敢的人。走进子午岭,他把自己变成了一个小矮人,不断穿越其中,童话与现实彼此交错;每一首诗里都有故事,每一个故事背后都有无声的童话。
自然,这也是一本写给孩子们的书。
子午岭永远是一个浑然一体的自然存在。子午岭之美,不仅仅美在生态,还有和谐之美。
众多“小人物”擎起了《绿子午》的精神世界
《绿子午》记录了桥北林业系统一个三代护林人的故事:“老林”任泰祥为了让儿子子承父业,生了第一个孩子后,起名建林;生了第二个孩子后,起名育林;生了第三个孩子后,起名成林。这三个孩子的名字,不但代表了子午岭森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三个生长时期,还成就了他的期望——让三个孩子都在子午岭深深扎下了根。如今,任泰祥已经去世,但他的三个儿子,除了一个已经内退,其他两个还在各自的岗位上。
翻阅全书,“林三代”并不是一个令人陌生的称谓。子午岭巍峨,子午岭人更是不凡,子午岭人为我们的生态福祉所付出的一切,青史不可忘记。
高凯说,大森林的根是树木之根,但归根结底是子午岭人的根。森林之大,是因为子午岭大;子午岭之大,是因为许多天南地北的人都把根留在了子午岭。如果没有一代代子午岭人的坚守,绿绿的子午岭就无法呈现出来。因此,高凯在动笔之前就暗下决心,要为子午岭的小事和小人物树碑立传。果真如此,出版后的整部作品所呈现的并不是大事,而是侧重历史的细节——许多小事及小人物,以此来反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子午岭的变迁。
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书记处书记、著名作家李敬泽说:“横跨陕甘两省的子午岭,昔日是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摇篮,今日是西安、陕北和陇东的绿色屏障,历史贡献卓越,生态意义重大。《绿子午》反映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子午岭生态文明建设的伟大成就和林业一线职工植树造林改天换地的伟业。这样一部长篇非虚构作品,是高凯这样一位优秀的诗人和报告文学作家,深入生活的又一个重要成果,它既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文明理念,同时也体现了中国作家、甘肃作家反映新中国成立以来和新时代以来中国人民创造历史的伟大实践。鉴于这一创作成果,我向高凯表示祝贺,并向子午岭林业人致敬。我相信这部书,会将子午岭的故事带给全国的广大读者。”
众多“小人物”入书,一代代子午岭人吃苦、坚守和奉献的精神跃然纸上。作品语言朴素流畅,事例选取鲜活,感情充沛,是一部难得的长篇报告文学力作。作为第一部全面反映子午岭生态文明建设的报告文学,《绿子午》不仅是陕甘子午岭人的创业史,还是中国护林员的心灵史。单行本出版之前,部分章节去年以来已经在《中国校园文学》《光明日报》《人民日报》海外版和《人民文学》等国家级报刊发表并产生广泛影响。这些作品的发表,使《绿子午》提前在子午岭产生回声。(文/禄永峰)
高凯简介
高凯,1963年出生,甘肃合水人,作家、诗人,现任甘肃省文学院院长、甘肃省作协副主席,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政协甘肃省委文史委员会委员、中国作协会员。从事文学创作40年来,出版《心灵的乡村》《纸茫茫》《乡愁时代》《高凯诗选》《童年书》《拔河兮》等诗集、散文、报告文学和绘本等著作18部。
返回顶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