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迹的高家堡
2021-10-19 09:22:36
来源:西部决策网
从文化的意义上来说,一切发生过的,都不会真正彻底消失,只是被层层沉积在历史的深处,历久而弥深。历史上发生的所有声音、色彩、关系、情感、认知、经历,从宏观到微观的一切,其实都安放在它们被存储的地方。当某种时空的震荡发生,历史潜意识的沉渣泛起,很多久远以前的元素,还会再鲜活起来,如附体一般在某个当下进入人们的意识,掀起内心的波澜,乃至能非常有力地以群体觉知涌动的方式参与到历史当中。
任何一个历史积淀深厚的地方,都是这种元素的宝藏,却不是每个人,都有缘分进入这种宝藏隐秘的入口。
陕北神木高家堡就是这样一个地方,陕北四大名堡之一,积淀了千年的历史,康熙皇帝还敕封这里的城隍为“灵应侯”,三品正堂,赐着冕旒衮服,十六抬黄轿,半副仪仗执事。
萧迹是高家堡的有缘人,这渊源从何而起,已经无法钩沉,2014年他浮光掠影从这个古堡短暂经过,2016年再来的时候,他在高家堡遇到了姓杭的一家人,就是这家人,成为他进入高家堡记忆的门户,他们在他耳边所说起的些许,和他意识深处本就存储的更多,一起在纸上流淌出来,成为了他的第十三部长篇小说《高家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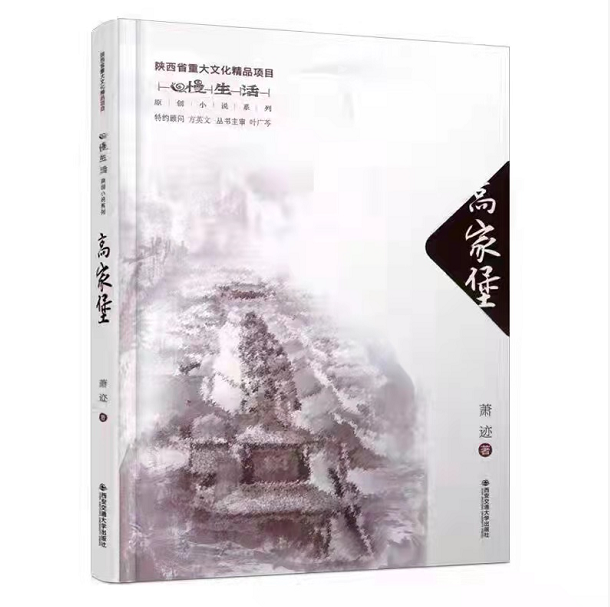
萧迹先生的文缘很重,而且写作风格非常富于变化,十几部书几乎没有哪两部是主题接近的,每一部的创作都是一次截然不同的创新,在他的创作中很难找到一以贯之的特征,在文学史上很难找一个类似的先例来进行比较,却恰好与当下时代意识前所未有的碎片化两相印证。和大多数困守主观深钻牛角的人们不同,萧迹拼尽全力打开视野去追逐时代快速演绎的种种变化。就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生的一代作家的知识结构而言,这样的追逐会是很艰辛的,而且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绝望地放弃了宏大叙事,掩饰着自己迷茫,选择一个小小的方向,凿通一段是一段,在狭隘的局部积攒有限的共鸣,防守着自己的合理,对其他方向的声响充满警觉与敌意。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历史局限,每一代人也都在寻求突破自己的历史局限。萧迹是典型的山东性格,灵魂里几乎没有会弯曲的纵深,这使他不太擅长于掩饰,敏感的内心不得不直面加速复杂化的世界,这个互动会非常摩擦,接触面的扩大使信息量变得极大,这确实很累,但也确实印证了更多,就此而言,萧迹对自己的历史局限突破得肯定比一般人更多一些,他身上的现代性也就更多了一些。
萧迹的每一本书能带给人的触动并不是特别强烈,他的力度在于系统,这个系统还在完工的过程中,《高家堡》肯定还不能算作他的代表作,这只是他整个文学格局的一个新组件,集大成的创作,就是由这一个个组件集结而成,那会发生在他文学生涯的巅峰,那一次创作,会有力撼动人心,那将是他人生的决战。

《高家堡》这部小说本身,虚构的是20世纪30年代以来这块土地上发生的故事,萧迹在这本书的后记中说:“这部长篇小说里高家堡的砖,石卯山的土,秃尾河的水都是真实的,其他的都是我从千千万万个中国农村把那些早已消失于历史云烟的灵魂一个个请回来,让他们在高家堡这座古老的城堡里复活,用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演绎出一部中国百年历史的缩影。这是一座我心中的高家堡,一座城,一座古城,一座有灵魂的古城。”
如前所说,每一段记忆都在努力进入现实,每一种现实也都在搜集记忆,在我们这个千万年来前所未有的特殊历史时期,历史与现实的互动过程也呈现出极其特殊的景象,有很多现象,甚至还没有相应的概念可以应用于描述。就像底蕴深厚如高家堡的过往,进入现实历史的触角之多难以计量。很多很多的陕北人头脑中都带着一部分高家堡,然后行走去世界的无数角落,结下不同的缘分。也有很多缘分每天从四面八方向高家堡而去,加入它的历史。萧迹的《高家堡》基本属于后者,但和经济元素的进入不同,萧迹的小说给高家堡真实的历史浪漫地涂上了一抹虚拟的时代色彩。这至少对高家堡的人们,就有了不一样的文化意义,也因此会有不一样的生命体验,这种体验是可以传承的。这类似于精神激活的过程还没有准确的文学术语来进行描述,这和魔幻现实扭曲到难以辨识是不一样的,是真实历史觉知的虚拟表达。

《高家堡》里的每一个角色,高铭琪、杭老先生、周宝恩、彦萍、灵芝等等,以及这些角色互动的故事,都不是凭空而来,都是萧迹自己所开阔的视野中捕获的信息的加工物,这些信息来自于纷繁复杂的历史与现实,在情节的演进与情景的细节中,表达的是萧迹对生活的觉知与判断,所有的表达,都是萧迹内心的样子。
这种创作的主观性,也是这个时代我们所说的文学表达的一个重要特征。
文学表达有无穷的层次,最顶级的表达是主张,里面有明确而坚定的东西;其次是描述,虽然混沌,但生动而活泼;再其次是呻吟,客观属性非常少,构建缺乏精致性,局限于主观情绪。再其次,那就不属于文学了,只能算是语言。与历史的周期律相应,每一种文学表达层次都有当道之时,也各有其历史合理性。就像我们这个大密度与高透明度的时代,有自己相应的声音,娱乐属性获得了很长久的合理性,而娱乐一般只存在于觉知的浅处,所以文艺的种种形式都以浅表为美,稍有深入,便会被人们本能排斥。不管人们的理性被灌输多少合理性,觉知却是诚实的,有怎样的视听体验当下便知,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这不是成长性的,是迎合,不是学习,是消费,文艺体验的主观性就由此而来。不过历史演变得很快。这个时期正在被结束,逐渐加码的压力体验把人们驱向更深一层的觉知,文学将会被另外一批规律性所主导。
在上一个潮流性的群体阅读共同体验碎片化之前,有很多典型性的底层逻辑,那是撑起《平凡的世界》、《白鹿原》、《废都》等壮观文学现象的社会基础,之后经济发展拆解了那些基础,所有的观念加工人都只能在浮沙上建塔,徒劳的艰辛决定了很多人的命运。萧迹的《高家堡》依然不能获取到足够的底层逻辑支撑,每个角色都很难生成鲜明的、酣畅淋漓的爱恨情仇,这本书所演绎的情节很难获得排山倒海的传播力量,因为人们内心并没有准备好足够的共鸣,所有人都局限在自己命运的具体细节之中,各有混沌,还不到共享某种表达的时机。所以不仅是《高家堡》难以表达出时代的典型性,这个世界上在不同主题中创作的作家们皆是如此,如果有个不一样的,不用解读,我们每个人自己都能看得见。即使诺贝尔的贴标也骗不了人,因为每个人的创作水平虽然差异很大,但同一时代的人们的鉴赏水平是接近的,另外真正有力的传播,和受众的耳目关系也不大。
在陕西省作协的大院里,有块石头上刻着陈忠实一句话:“文学依然神圣”。其实这句话能被说出来的时候,相反的也事实已经开始发生了。所谓神圣是某种有落差的引领力,当狂欢开始的时候,神圣会开始变得苍白。陈忠实在他特殊的年代登上了自己的神坛,而学他的人,却需要穿越一个意想不到的低谷。贾平凹说小说就是说话,这种就低的表达使他深深谷底高高山上自由行走,但他依然是一个靠体量创造高度的大神,和那些真的把说话当成文学的人们截然不同。在更深远的历史中,他的名字与作品会不断找到印证之物,其他那些在狂欢中迷失自我的人,无法获得这样的文化寿量。
萧迹先生持久的文学创作与贾平凹相似,只不过各自穿越的是不同的时空,交集的部分恰是这个行业的低谷,历史赋予贾平凹那种独特的审美价值,在这样的低谷大家都获取不到,只能付出更大的努力去维系一种微弱的声音。任何现象级的事物,其实都是历史机缘首先把它成就,然后选择某些进行了充分准备的个人作为标签,当历史条件并不具备的时候,能以一己之力成就一种气候多是一种痴心妄想。尤其在低谷的行业,集体的力量更加重要,愈向上攀升,个人舒展的空间才可能更大一些。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部《高家堡》,正如一千面镜子互照,其实每一面镜子都能收摄到全息的影像,只不过绝大多数人并无内因外缘进行这样的创作而已。但每个人的《高家堡》都在来叠加的路上,碎片化的时代正在结束,裂变生成能量的过程将被聚变生成能量的过程所取代,完整性的审美价值正在回来,那将是更有尊严和更加和谐的体验过程,贫瘠心理的很多残余将会被充分治愈,静穆的价值将会被广泛接受,与全新的经济基础相适应的思想意识将与爆发过程中狂欢的心态有很多不同。
我觉得萧迹先生的创作是离下一个阶段的演化是最接近的,他所已经打开的视野注定了某种更有建设性的创作的发生,很荣幸与这样的演化共进,期待更精彩的表演。(张波)
返回顶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