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津关:锁控峡江的千年雄关

在长江三峡东口,西陵峡与江汉平原的交界处,南津关如一道青铜屏障,横亘于湖北宜昌西陵峡口。这座“上控巴蜀,下引荆襄”的千年关隘,以“水至此而夷,山至此而陵”的地理密码,成为长江中游的咽喉要冲。它是三国烽火的见证者,是文人墨客的抒情地,更是中华文明在峡江地带写下的壮丽注脚。
一、地理形胜:峡江锁钥的天然壁垒
在长江三峡东口,西陵峡与江汉平原的交界处,南津关如一道青铜屏障,横亘于湖北宜昌西陵峡口。这座“上控巴蜀,下引荆襄”的千年关隘,以“水至此而夷,山至此而陵”的地理密码,成为长江中游的咽喉要冲。它是三国烽火的见证者,是文人墨客的抒情地,更是中华文明在峡江地带写下的壮丽注脚。南津关位于宜昌市夷陵区西陵峡东端,北倚荆山余脉,南接武陵丘陵,因三国时期刘备驻守津口南岸得名,明代设巡检司后固定为“南津关”。此处为长江中上游分界点,葛洲坝修建前江面宽约200-300米,出关口后骤扩至2000余米,形成“峡口锁江,豁然开朗”的独特地貌。《水经注·江水》载:“(江水)径宜昌县北,县治,故刘璋所置也,为峡口重镇”,道尽此处“承峡江险峻,启江汉平阔”的过渡性地理价值。
作为长江航运的关键节点,南津关西连巴蜀盆地,东接江汉平原,自古是“蜀道难”的东端出口。战国时期,楚国在此设“夷陵邑”,取“水夷山陵”之意,既指江面在此由险变夷,亦含“以险制夷”的防御意图。宋代《太平寰宇记》称其“当水陆之会,控荆楚之咽喉”,精准概括了其“一关分险夷,两域通南北”的战略地位。
二、历史烟云:战火淬炼的军事重镇
南津关的历史,是一部浓缩的峡江攻防史:
1. 三国猇亭之战:火攻定鼎的地理宿命(222年)
蜀汉章武二年,刘备为报关羽之仇东征孙吴,在西陵峡口至猇亭(今宜昌猇亭区)一线与陆逊对峙。尽管主战场位于猇亭,但南津关作为峡口门户,是蜀军后勤补给与水师屯驻的重要据点。陆逊采用“火攻”破敌,“火烧连营七百里”的谋略虽未直接发生于关隘内,却依赖对峡江气候与地形的精准把控——南津关的险峻间接成为战役胜负的地理注脚。战后,孙权在此设“西陵督”,筑城屯兵,南津关正式纳入东吴长江防线。
2. 晋灭吴之战:楼船破锁的峡江传奇(280年)
西晋大将王濬率楼船水师顺江东下,吴国在西陵峡口“以铁锁横截江面,作铁锥暗置江中”(《晋书·王濬传》)。尽管史载未明确南津关是否为铁锁防御点,但其“峡口锁钥”的地位使晋军必须突破此险。王濬以“大船载草,灌以麻油,火焚铁锁”,最终破吴国防线,南津关见证了中国古代水上攻防战术的巅峰对决。
3. 抗战峡江阻击战:近代国防的最后屏障(1938-1943年)
抗日战争时期,南津关成为拱卫大后方的关键防线。国民政府军在此构筑炮台、战壕,依托西陵峡险峻地形,与溯江而上的日军展开五年拉锯战。1943年“石牌保卫战”中,南津关至石牌一带的绝壁天险,使日军“三个月打通长江航线”的图谋破产,成为“东方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核心战场,至今仍存的碉堡与战壕遗址,诉说着近代中国的不屈精神。

三、文化脉络:峡江诗路的精神地标
南津关的壮丽风光与历史厚重,吸引无数文人墨客驻足抒怀,形成独特的“峡江诗路”:
李白的仗剑天涯:“楚水清若空,遥将碧海通”(《江夏别宋之悌》),李白乘船过南津关,见“山束江欲断,开帆出峡门”的景象,写下对峡江豁然开朗的惊叹;
白居易的峡江感怀:《初入峡有感》“上有万仞山,下有千丈水。苍苍两岸间,阔狭随石势”,直接描绘南津关“峰回水转”的险峻与壮美;
陆游的纪实书写:《入蜀记》详细记载南津关风貌:“(西陵峡)两岸高山相峙,云雾缭绕,水势奔涌,过南津关如出牢笼”,并记录宋代关城“置巡检司,驻兵百人,司峡口之险”。
除了诗词,南津关孕育了独特的峡江号子。船工在西陵峡的急流险滩中,以“嘿唑、嘿唑”的号子协调动作,其节奏既是生存的协作信号,也是对峡江天险的生命赞歌。2006年,“长江峡江号子”入选首批国家级非遗,其传承核心虽覆盖整个西陵峡,但南津关作为峡口枢纽,成为号子文化的重要传播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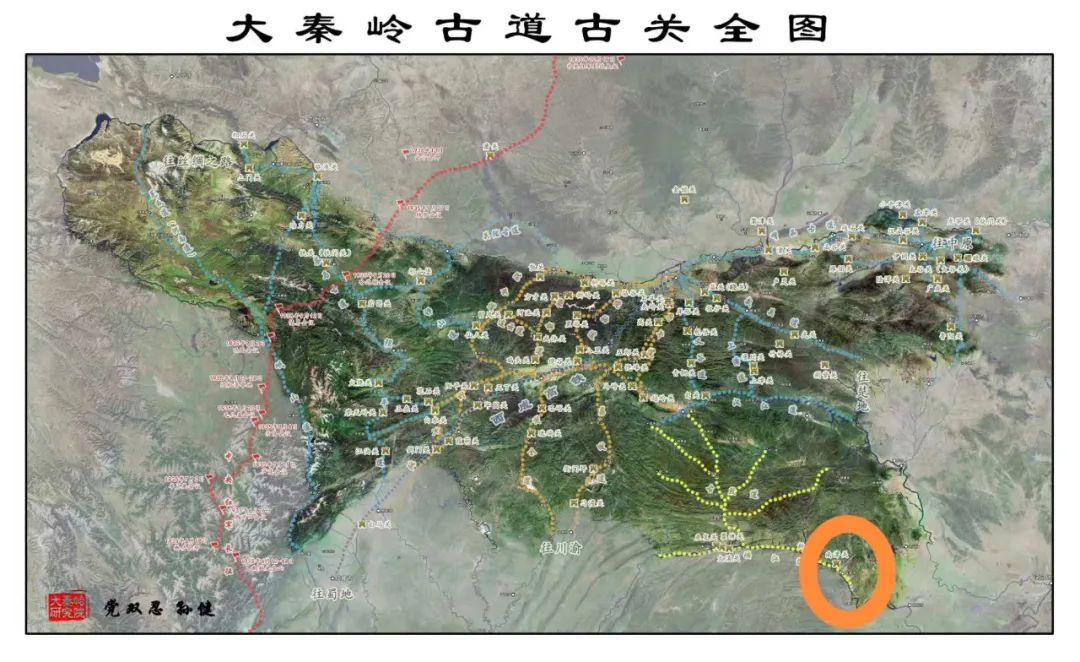
四、古今交响:从战场到文旅的时空转换
20世纪以来,南津关因水利工程与文旅开发迎来新生:
1.水利工程重塑峡江格局
1981年葛洲坝建成后,南津关水位提升20米,昔日“滩如竹节稠”的险滩沉入江底,却造就了“高峡出平湖”的奇观。2006年三峡大坝全线建成,万吨巨轮可通过五级船闸平稳过峡,南津关从“舟行如箭,险象环生”的天然屏障,转变为“天堑变通途”的航运枢纽,却仍以“三峡东口第一关”的姿态,俯瞰着江面的云卷云舒。
2.文旅融合的峡江叙事
如今的南津关景区,整合自然奇观与历史记忆:
古关文化区:复建的“南津关楼”高15米,青砖灰瓦间镶嵌三国时期的青铜戈复制品,楼额“南津关”三字取自宋代摩崖,两侧楹联“锁三峡东口,通九州航路”重现关隘雄风;
战争文化体验馆:通过VR技术还原三国火攻、抗战阻击等场景,游客可“操控”古战船穿越险滩,感受“以险制敌”的军事智慧;
峡江徒步道:沿西陵峡北岸开辟的古纤道,串联起“三游洞”“灯影石”等奇观,途中200余处铁环遗迹(供船工攀岩拉纤),与现代游客的徒步轨迹重叠,形成“千年纤夫路,今日文旅径”的时空对话。
2020年,南津关所在的“三峡人家”景区升级为国家5A级,年接待游客超200万人次。当游轮驶过南津关,乘客既能在甲板上远眺“截断巫山云雨”的大坝雄姿,也能在关楼前聆听非遗传承人演唱峡江号子——古老关隘在新时代焕发出“以文塑旅、以旅彰文”的勃勃生机。
结语:在险夷之间看见文明的通途
南津关的千年变迁,是一部人类与长江对话的史诗:它曾因“险”而成为战争的熔炉,却也因“夷”而化作文明的通途。从三国的烽火到今日的平湖,从“猿鸣三声泪沾裳”的险阻到“高峡出平湖”的奇迹,南津关始终在“险”与“夷”的辩证中,诠释着中华文明“知险而不畏险,遇夷而善用夷”的生存智慧。
站在西陵峡口,看长江水奔涌东去,南津关的城堞在云雾中若隐若现。它是地理的隘口,更是文明的渡口——曾经,它见证了金戈铁马的壮烈;如今,它承载着山水相连的希望。正如长江从未停止流淌,南津关的故事也在继续,诉说着人类在自然天险中开拓通途、在历史烟云里守望未来的永恒追求——这,正是峡江锁钥留给世界的文明启示。(文/党双忍)

2025年6月15日于磨香斋。





